新闻中心 /News 
史学专论 || 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ky开元旗牌官网
【学者概述】孙宏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学科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与政治思想史、中日关系史,著有《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进行——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年出版)等,并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沃勒斯坦、狭间直树和山室信一等学者的理论思考及其涉及研究提醒我们必须从一些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来探究19 世纪发源于欧美的社会科学的科学知识范式,是如何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展的同时发展与蔓延,进而规训了非欧美国家的学术体制乃至塑造成着新的政治传统。
这似乎是极为可观的研究工程,作为这项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有适当对源于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文本在其他地区的翻译成和传播情况展开系统的调查和整理。本文探讨于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学名作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可译作《国家的历史和实际》,以下全称《国家》),调查其在近代中日两国的翻译成情况,除了考据和讲解各种译本信息,也对译者身份和翻译成动机加以分析,借以勾勒威尔逊的《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成史,并期望将来有可能更进一步进行各文本内容、译语和翻译成策略的较为研究,以及译本的读者和传播史,进而辩论其政治学科学知识对于近代东亚的政治变革和国制塑造成的影响。一、威尔逊其人及其政治学著作《国家》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2月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镇(Staunton)。
16岁转入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后因病退学。1875 至1879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自学文学和政治学。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法学院自学法律,但一年后即因身体健康原因被迫休学。1882年同友人合伙在亚特兰大开办了律师事务所,由于业务不欠佳而于次年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所自学历史和政治学,188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于1885—1888 年、1888-189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玛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和康涅狄格州的威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讲授历史和政治等课程。1890年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兼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于1902—1910年兼任校长。
曾兼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09-1910年)。1910年被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被选为美国第28任总统,1916年顺利参选。
1924年逝世于华盛顿。(威尔逊)威尔逊在攀上政治舞台以前,具有二十多年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经历,著作非常丰富,还包括《联邦议会政治》(Congressional Government,1885)、《国家》(The State,1889)、《美国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02)、《美国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08)等,是颇负盛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并被视为美国“新的政治学”(New Politics)的先驱者之一。
美国政治学在1900 年之前,由于受到欧洲学术的影响,先后经历了先验的、演译的和历史的、较为的两个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其他新兴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影响暗喻了人们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再加美国国民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及实用主义的精神,还有以文官制度为中心的行政改革的影响,使政治学渐趋注目美国现状,推崇宪法、美国政府和市政学,历史的、较为的研究方法很快衰败,而趋向仔细观察、调查与测量,心理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也开始经常出现。在美国政治学史上,威尔逊的政治学大约可以以定坐落于第二阶段,即主要展现出为对政治现象展开历史的和较为的研究,同时也主张和推展政治学向第三阶段即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向发展。1966年9 月,阿尔蒙德(Gabtiel A. Almond)在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讲中谈及倡导“新的政治学”的先驱者威尔逊等人的学术思想特征:“在19 世纪后期,随着在学院里的专业化政治学的发展,对理论的有效性产生了猜测。
伍德鲁·威尔逊、A·劳伦斯·洛厄尔、弗兰克·古德诺,特别是在主张在政治结构和功能之间做到更加明晰的分析与区分,希望使经验政治学从以往指出在二者之间具备种种必定关系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威尔逊和古德诺具体地敌视政治和行政之间的三分区别,而赞同二分的区别。……这些政治学者们,都拒绝接受形式主义——不论是法律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而反对对事实——实际的运作、继续执行和行动等展开研究。
”1887 年,威尔逊公开发表《行政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具体阐释了他对于发展美国政治学的基本看法。他说道:“根据现代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宪政史来看,可以说道在当前发展程度最低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其他所有的政治体制也不会如此。
其中,第一个时期是意味著统治者时期,行政系统适应环境于意味著统治者;第二个时期是制订宪章以废止意味著统治者并取而代之民众掌控的时期。在这世纪末中,行政管理被忽略了,因为人们更为担忧制宪和废止意味著统治者这样的一些目标;第三个时期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彰显他们权力的新宪法的确保下,专门从事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我们早已抵达了第三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人民与专制权力斗争,为自己夺得了宪法。
现在,他们必需发展行政管理以与宪法相适应。但是,我们还没为此而展开打算。——这是他敦促美国急需积极开展行政研究的出发点。
而他指出行政习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的建构。英国人“致力于掌控政府而不是强化政府,更加关心的是如何使政府公正、保守而不是使它简捷、有序和高效。
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史不是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而是法律监督的历史——不是政府的组织的变革史,而是制订法律和政治评论的历史”。忽略,“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一起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的组织森严的国家的必须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环境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而创建一起的”。那么,否意味著美国也应当回头法国与德国的政治道路呢?威尔逊的问则是:“所有明智的自由选择都会是拥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道路,而不是任何欧洲国家的道路。我们会去经历普鲁士的历史而为了取得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技术;而且普鲁士类似的行政管理制度会令我们窒息而死。
与其卑躬屈膝和循规蹈矩,还不如予以训练和自由自在。然而不可否认另有更佳的情况,那就是既具备权利精神而同时又通晓管理实践中。
”这就引向了他对于政治与行政两分的阐述。他指出“行政管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要求了行政管理的任务,但却没适当去操控行政管理机构”。这某种程度也限于于“宪法问题”和行政管理问题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行政和政治的区分,他指出在行政学领域中用于较为方法是可信的,“当我们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制度时,由于我们坚称自己不是在探究‘政治’原理,因而当法国或德国人向我们说明其行政实践中时,我们不用在乎他们就宪法和政治方面的理由所做到的撒胡椒面式的说明。……只要把研究行政管理作为前进我们的政治便于实践中的一种手段,作为使面向所有人的民主政治在行政管理上也需要照料到每一个人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就不会正处于十分安全性的基础上,而且就需要自学外国制度必定会教给我们的东西而不犯错误。
”他具体地回应:“为了适应环境我们的目的,对法、德的行政学必需展开改建,使之合适一个简单多样而不是单一集中于的国家,而且适合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形式。如果我们要应用于这门学问,我们就必需使之美国化,不是在形式上或意味着从语言上,而是必需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彻底加以美国化。它必需从内心深处了解我们的制度;必需把官僚主义的热病从其血管中加以回避;必需多多排出美国的权利空气。
”威尔逊的上述观点是他文学创作《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解读该书要旨的关键。《国家》出版发行于1889年,正文长达656页。作为政治学的教科书,威尔逊实在有适当在序言里对该书的撰写体例和阐述范围稍加提醒。
首先,他断言此前不不存在与该书具有某种程度目的和范围的教科书。他本想要简练易懂地描述近代的政治机关,权利地辩论政治的一般原则和各种制度的详,但考虑到缺少适当的参考资料,被迫用相当大篇幅去陈述明确的历史和事实,这就使得本书的篇幅过大。
为了引人注目该书的宗旨,他将正文中作为阐述事实和细节的大量相比较和解释用小活字的方式处置,这样便于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更容易做到文本的连续性而不至于受到细枝末节的影响。不过,这些小活字的段落和那些注释一样,都是与文本主体无法拆分的组成部分。在阐述历史的部分,仅限于篇幅和范围,无法尽悉其原委交错,因此还造就教师在讲授之际加以补足。
其次,他简要认为该书自由选择阐述的几种类型政府。他说道,在研究现代政治之前,必需理解有所不同类型的古代国家政体。法国的政府是中央集权制为的一种很好的例子,英国是中央集权制为的又一种例子;德国是联邦帝国,瑞士是一种联邦共和国,美国则是另一种联邦共和国;奥匈是欧洲独特的目前为止不存在的双头君主制,而瑞典—挪威则是这种双头君主制于晚近和平解体的唯一例子。
俄国毫无疑问也是欧洲政治的一分子,也应当有一章不予论析,但是无法因此而增大该书的篇幅了。事实上,即使是两册这本书的规模也完全无法容纳更好的章节来阐述欧洲各种行政的和立宪的的组织制度。再度,他谈及该书的研究方法。
他期望这本书因为具备较为政治学的趣味而能为政治学教师所拒绝接受。他说道,较为政治学最近几年在英语国家里大不受希望,在美国各大学竞相热衷政治学研究之际,较为政治学转入教学的门户堪称是及时的。因为只有那些理解他国的各种制度和广泛制度史要点的人才能解读和喜爱美国的制度。
而且,运用较为的和历史的方法可以取得关于制度的具体的科学知识看法。由于制度中普遍的相似性和政治中完全相同的方法——这种在结构与过程中的一致性是制度研究初学者无法找到的——的显出,夺权了许多将主权国家的制度视作独有的、极致的专横之论。
因此,注意到各种制度的一致性,那么其间之差异就更容易被找到,于是其国民性格和历史有所不同的原因也就更容易被说明了出来。差异多展现出为国民的特性异质,其相似之处则表明各国联合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基于便捷的普通原则或仿效的道理。因此,可以断言研究政治学的方法只仅限于较为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这是无可争辩的。
最后,威尔逊回应这本书对近代政治的阐述主要是倚赖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教授海因斯·马卡德森(Heinrich Marquardsen)新近编辑出版的《现代公法手册》(Hand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序言虽然结尾,但是简要交代了《国家》这本教科书的用于范围和用于方法、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参考资料。其目的是要从欧美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寻政治的广泛法则和行政原理,所用于的研究方法则是较为的和历史的方法。
对照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说道《国家》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种观点的伸延与实践中。至于威尔逊的这种新的政治学思想的来源,内田剩特别强调其不受英国政治学家巴吉浩特(Walter Bagehot)的影响。
威尔逊曾以巴吉浩特的《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为范本,编写了《联邦议会政治》(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论述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按英国的政治体系所获取的模式加以改革的适当。巴吉浩特的《英国宪制》同他的另一部名著《物理与政理》(Physics and Politics)一样,其主要特征是利用政治事实和现象,探究实际运作的政治结构及其活动规则与运营方式。与此同时,威尔逊也特别强调历史方法的重要性,这应当与他曾多次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所自学的经历有关。
在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指导下,霍普金斯大学把德国国家学以及历史的方法作为其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亚当斯曾到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伯伦知理(Johann K.Bluntschli)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
故在创设初期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会议室里所通告的正是特别强调政治学和历史学密切关系的箴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所展现出出有的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present history)。所以低田早苗曾盛赞威尔逊习兼任英、法、德历史学派,堪称美国新的学派之泰斗;其识见高迈、文章雄浑,不想于英国的巴吉浩特。1909 年威尔逊就职美国政治学会第六任会长(1909-1910),体现了威尔逊在美国“新的政治学”界所具备的领导地位。
二、《国家》在日本的译介将威尔逊的《国家》一书译介到日本的主要是低田早苗(1860-1938)。低田早苗早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自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习历史。
当时东大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课程都是由美国人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一人兼任,讲授的内容主要为利伯(Francis Lieber)和乌尔希(Theodore Dwight Woolsey)的政治学、边沁(Jeremy Bentham)的政治哲学、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原论,以及康德、黑格尔的哲学。1882 年7 月低田从东大毕业,旋即参予创立和经营东京专门学校(1902 年改名早稻田大学),沦为该校政治学的核心教员,活跃于政治学的前沿。(低田早苗)低田早苗在东京专门学校前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兼任的教学科目甚多,作为课程讲义刊印的就有《英国行政法》《英国政典》《英国外交政略》《英国宪法史》《国会法》《政体论》《英国宪法》等,多为现学现卖英国学说。此外,他还编有《通信教授政治学》。
这是低田最初的政治学著作,也具备英国政治学的特征。1894 年,低田早苗就职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部长,的组织刊印“早稻田丛书”,并之后兼任教学工作。
这时他开始注目美国的政治学,在英语政治科开办的课程“伯吉斯政治学”,主要讲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创始人伯吉斯(J. W. Burgess)的著作《政治学与较为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并将威尔逊的《国家》翻译成日文,书名所取“国家学泛论”,作为政治科第一至第三年级的讲义录(明治二十六-二十八年)。接着又将该译本书名改回“政治泛论(一名沿革简单政治学)”,列入“早稻田丛书”第一系列(共10部)之首,于1895 年10 月刊印,由此冲破了“早稻田丛书”的出版发行序幕。到1909 年,“早稻田丛书”共计出版发行了43 种译著。
其中归属于政治学的有15 种,按著者国别区分,英国5 种、法国2 种、德国1 种、美国7 种,显著偏重于英美政治学著作。作为讲义记的《国家学泛论》可以说道是全译本了,还包括了原著的16 章内容,共1 220 页,只是没看到序跋之类的文字。而列为“早稻田丛书”的《政治泛论》既有威尔逊的原序,又有低田早苗编写的译者序,在同书的卷首还刊登了据传是低田特地撰写的《早稻田丛书出版发行趣旨》。
其中,除了谈及以本国语言对各专门学科展开教学和翻译成以采纳日新的变革的西洋学问的最重要意义,也传达了翻译成的态度与标准:“本校拒绝翻译成不应极具准确性,且以朴实清了为宗旨,所译之物否符合标准,不但该文之所写翻译者要回应承担责任,而且本校校方亦当甘负其责。”在译者序里,低田说明了自由选择威尔逊的《国家》展开翻译成的目的与缘由:《政治泛论》的著者Wilson是美国出名的学士,尝著Congressional Government,痛论合众国政体之利害,欲声名幸扬。
长年在美国第一流大学Johns Hopkins教授政治学,其钻研磨练的结果终因《政治泛论》以求问世。Wilson习兼任英、法、德学,科历史学派中人,但未拘泥于此。他眼光灵敏,论评诙谐,且其所见亦朴实公平,实乃美国新的学派之泰斗。余曾拜读Wilson之Congressional Government,感觉其人即美国之Bagehot,其胆识之高迈、文章之雄浑多远不如Bagehot。
前几年,友人家永丰吉自美国学成归来,示其所携之The State,余读书之,益觉Wilson毕竟奇怪之学者。欲据家永之书著手翻译成,几经四载星霜,再一完稿。然余事《政治泛论》之译为,非惟推服其人之学识,亦思填补我邦政治学研究上之缺乏。我邦政治学研究虽日新月盛,而必要之教科书则寥若晨星,坊间所见亦不过Bluntchli之《国家论》、Rathgen之《政治学讲义》等数种。
本来不惟我邦缺少解释政治学简要之必要的教科书,即在英美德诸国亦不夥闻。此书在外国既然都是屈指可数之孤本,毫无疑问更加不应沦为我邦政法学生之宝典。加之近来时势日新的,政治之实际不可不与政治学理益加紧密,当此之时,坚信本书当为大方士君子座右不可或缺之要不具。
……读书此书者不仅可以自学政治学原理,亦能通晓各国制度,便于较为研究其利害利弊,此为其所以高于一般政治学教科书之一理由。从以上所谓之序言的部分内容来看,均可闻低田早苗对威尔逊推许之低,其中还提及威尔逊的学术特征,并将其与英国的巴吉浩特相提并论,定位为“历史学派中人”和“美国新的学派之泰斗”。1895 年12 月,低田早苗致信威尔逊,威尔逊于次年4 月6 日恢复低田,并依高田的心愿寄给其个人小传和照片。在1896 年11 月发售的《政治泛论》第三版卷首里所提醒的“伍德鲁·威尔逊略传”和威尔逊的照片以及写信给的影印件即由来于此。
此后,两人虽有两三度书信来回,但终未谋面。直到1914年9月28日,当时早已是早稻田大学校长的高田早苗在其“欧美漫游”旅次中,再一有机会去白宫造访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政治泛论》从1895 年首次公刊到1916 年更正修编出版发行,其间重刊了十余版。各版的具体情况无法一一尽悉,不过有一点提到的有1908 年刊印的“经世七大名著”本和1916 年刊印的更正增补本。
1908 年10 月20 日是早稻田创办二十五周年纪念庆典,作为一项纪念,校方特设专人对“早稻田丛书”已刊行译作展开审查会,并借此指定了可作为盛世经典的7 种图书,经绵密精细的校勘,冠上“经世七大名著”再行刊行。这七大名著是:1.《政治泛论》;2.《较为宪法论》(J. W. Burgess著,低田早苗、吉田巳之助译);3.《较为行政法》(Frank J. Goodnow著,浮田和民译);4.《经济原论》(英国Alfred Marshall著,井上辰九郎译);5.《财政学》(英国Charles Francis Bastable著,井上辰九郎、高野岩三郎译为);6.《今世欧洲外交史》(法国Antonin Debidour著,酒井雄三郎译为);7.《国际法》(俄国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著,中村入午译为)。其中前三种为政治法律类,著者分别是威尔逊、伯吉斯和古德诺,可见低田早苗对于美国政治学尤其是威尔逊的《国家》一书的态度。低田早苗新的为该版《政治泛论》不作了序,除了比以前的序略为详尽地讲解了威尔逊的学术和教学经历,还鲜为人知了他翻译成《国家》和发售“早稻田丛书”的动机与贡献,进而提及再行刊行“经世七大名著”的目的:“当此早稻田大学创立二十五周年举行庆典之际,作为纪念,从早稻田丛书中精选辑七种永世不朽的名著,题以‘经世七大名著’刊印于世,大自然绝非其理由。
想起近年的学术变革和学术趋向,虽绝非尚之信之处,如数年前的玄学夸张之风日渐起至,曲学阿世之徒渐多,真诚笃实的学者也开始取得世人的尊重,但是国民的广泛风气或许还甚不完善,尤其是政治界,与十多年前比起,其主义和思想甚至有倒退的迹象。此时获取真诚的政治经济名著,作为与世间同具忧患之士共挽狂澜于将倾之策,实无其适当,坚信并非徒劳之荐。”1916 年刊印的更正增补本是低田早苗在“欧美漫游”之际托付给同为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大山郁夫来展开修改修编的。
高田在为《更正修编政治泛论》一书所写的序中尤其提及此事:当时,大山郁夫刚完结了从芝加哥大学到慕尼黑大学的四年求学生活,返回早稻田大学专门从事教学工作。他不应低田所须要,愿答允对《政治泛论》不作修改修编,欲对照原著的新版广受修改,而且还根据原著更新发售以后各国制度的变化和新的统计数据,并参照最近出版发行的书籍加以增补修编。因此,此版《政治泛论》与以前的版本比起,不仅纸页篇幅深感减少,而且记事内容和思辨也毕竟面目一新。在这版序言中,高田仍一如既往对威尔逊的学问人品和《国家》一书广受推崇。
称之为此书“涵括政治学之整体,详于学理与实际,为得之不易之欠佳看似”,“翻译成出版发行之际,为日本绝无仅有之此类著作”;“内容周密而深刻印象,论点流畅,全线贯通政治学之整体,令人对政治学的学理和实际一目了然”。“其价值之所以如此之低,实赖博士于讲堂累积了多年经验,又于书斋中醉心了无数文献,而且正值其思想成熟期,倾心于思维国家政治之体用关系,加之对材料的权衡决定简繁得当。这不仅在欧美众多政治书籍中是出众的,而且同类之不作也科较少,因此甚至连向以公法学者之渊薮而自豪的德意志帝国也将刊印其译作。
”新版《政治泛论》被列入“新的早稻田丛书”第1、2 编成,因为篇幅减小,分成上下两卷(册)出版发行。大于是以六年(1917)3 月1 日重印,大于是以七年9 月25 日三版。至于之后否还有新的版本,还有待调查。
纵观《政治泛论》一书在日本二十多年间的出版发行史,可见低田早苗对威尔逊《国家》一书的推崇是超乎寻常的,这在日本同期的学术界也是非常尤其的。其中的原因有一点思维,最少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低田早苗在东京大学的受学经历奠定了其与英美学术的渊源基础,而与德国国家学没必要认识。第二、他毕业后重新加入的党派——改良党以及专门从事教学研究的工作单位——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都归属于大隈吉田的系统,颇受英国学风影响。
第三、低田早苗对巴吉浩特早于有兴趣,而威尔逊的政治学研究则承继了巴吉浩特的学术方法与风格,但又旁及其他学派,这对高田毫无疑问更加具备吸引力。三、《国家》原著及其日译本《政治汎論》在中国的译介本节不对威尔逊其人及其论著与中文世界的认识交流史不作全盘的阐述,仅有就其《国家》一书在清末民初的译介情况稍加整理与较为。
目前就笔者熟知,在清末民初时期必要或间接译述威尔逊《国家》的中文译本共计以下几种(据版权页抄写):政治汎论(美)域鲁威尔逊著,顺德麦鼎华译为,下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中浣上海广智书局第一次刊行;上卷,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中浣上海广智书局第一次刊行。政治泛论政学丛书第二集第六编成,【著者】美国学士威尔逊,【原译者】日本低田早苗,【轻译者】商务印书馆,【校订者】鄞县章起渭,【发行者】(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首版。政治汎论【原译者】低田早苗,【轻译者】宁县章起渭,【改定者】武进王倬,【发行者】(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年三月初版。
政群源流录美国韦尔生原著,吴县李维格、新会伍光建同译,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南洋公学译为书院第一版。政治源流谢卫楼译为编,北通州协和书院印字馆镌,宣统二年。以上5种译本,前3种就是指低田早苗的日译本翻译而来,其余2种应当就是指英文本必要翻译成过来的。从时间上来看,南洋公学译为书院的译本最先。
南洋公学是1896年10 月由盛宣怀下诏在上海成立的一所新式学堂,1898年春筹设了译书院。译为书院的早期出版物偏重于实用性的书籍,后来这一方针有所调整,在张元济兼任译为书院院长期间,他先后主持人编译器了英国保罗、伯德台年出版的《中等算学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莫尔贞年出版的《算学读本》、美国韦尔生子的《政群源流录》、英国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英国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和下山宽一的《万国政治历史》等。
这一调整与时局的变化当有密切关系。清廷于1901 年初诏令变法并于4 月正式成立总办政务处,朝臣及州县于是试探着明确提出了一些改革政体的意见。1902 年秋,办理商务大臣盛宣怀曰日本、德国之政体可为效法,下诏多译为其政法书籍。这大约就是译为书院翻译成《政群源流录》等政法书籍的主要背景。
目前所见之《政群源流录》共2 卷。卷一也即“第一章原治”,分42 节;卷二即“第二章希腊政体”,自43 节至159 节。
卷二末尾录“卷三以下续出”,但否有续出有,尚能不确切。译者伍光建(1867—1943),广东新会人。1881 年毕业北洋水师学堂,在总教习严复指导下,接受严苛的中英文双语训练。1886 年毕业赴英求学,进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自学军事,一年后转至伦敦大学,1891年回国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
1905 年起多次随清政府官员使臣欧美日本实地考察政治和宪政。另一译者李维格的生平不可考。仅有从伍光建的教育学术背景来看,《政群源流录》毫无疑问就是指威尔逊的英文原著翻译成而来。从高田早苗的日译本翻译而来的3种译本只不过只是2种,因为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发行的2 种版本都是同一个译者。
麦鼎华的译本虽然没标明就是指高田的日译本译出过来的,但是只要较为一下两种译本的章节目录以及其中的汉字译语,就可以判断就是指日译本迻译而来。关于该译本的由来当然要联系康梁维新派立宪派的背景来看。康梁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到日本,旋即康有为不得不离开了日本,而梁启超则与其他康门弟子侧重舆论宣传和输出西洋法政科学知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和传播新的科学知识的平台,而由维新派经营的广智书局也担任了讲解有关君主立宪思想科学知识的任务。
在维新派立宪派译印的政法类书籍中,除了威尔逊的《政治泛论》外,还有那兹硁的《政治学》、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松平康国的《英国宪法史》、天野为之的《英国宪法论》、小野梓的《国宪泛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纲领》、非立啡斯弥士的《英国制度沿革史》等,均为广智书局提倡立宪的最重要读物。译者麦鼎华,字公立,广东顺德人,麦孟华之三弟,早年游学于康有为门下。
戊戌后逃往日本,进日本大学法科修读,毕业后回国,历任法官。1913 年康有为倦游归国,曾嘱麦鼎华与陈逊宜编《不忍心杂志》。
所译著作还有《中等教育论理学》《埃及近世史》等。在麦鼎华译本月刊印前后,《新民丛报》上频密经常出现该译为书的出版发行广告。在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发售的40 /41 号合刊上,“绍介新书”栏目下有一文专门对翻译成《政治泛论》的缘由和目的不作了讲解,并罗列了各篇(即各章)的标题目录(与译本略为有文字有所不同)。
文中写出到,“国民建国之元气,什意图政治思想,故政治学之要,尽人而知之矣。虽然,读书政治学书有数无以”,概言之,要么于事实过分简略,要么深奥抽象化,要么平庸,让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么片面主观,绝于真理。
“有此四难,故欲求一书适与吾中国今日学者之程度适当,使其读书一过而于政治上之大理了然无复凝滞者,诚戛戛其难哉。若此者,惟威尔逊之政治泛论,可以当之矣。此书当十年前,上海时务报馆已翻译成过半,后以事卒业,而其译稿亦复亡佚。
更加暇七八年,仍未得输出我祖国,实失望之近于也。而至今日本出版发行之政治书,汗牛充栋,惑懦弱出有其右者(就限于于中国学界论)。”(《政治汎論》 商务印书馆译本) 商务印书馆译本的再版版权页上标示“轻译者”为商务印书馆,“校订者”是“章起渭”,而1913年的版本则标明“轻译者”是“章起渭”,对章的籍贯记述也前后不一,尽管如此,应当可以判断章起渭就是轻译者。
关于章的身份,还有待考证,仅有闻他还翻译成过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和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还参予译校了《新的译为日本法规吉尼斯世界纪录》等。光绪二十九年的译本不告诉明确译为自高田译本的哪一个版本,但认同不是列为“早稻田丛书”的初版本,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这个译本里不仅有“政治泛论序”,还有“威尔逊略传”,而“威尔逊略传”是在1896 年11 月发售的日译本《政治泛论》第三版里才经常出现的。
商务的译本大约更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动机,不像维新派立宪派那样主要基于其推展立宪的理念和目标。因为当时新政实行旋即,科举改试策论、书院改设学堂等项变革措施不仅促成了射策市场对于新学的市场需求,也推展了学堂教科朝着培育政法财经人才的方向发展。当然,维新派立宪派也并非不考虑到商业利润。
据张朋园研究,广智书局的经营方式第一为译书,讲解西方文化,第二为出版发行科考应试指南,以不应士子之须要,并以后者扣除发展前项目标。协和书院刊刻的译本经常出现最晚,但它毕竟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器的,具备有所不同的意义。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1841—1913)是美国公理会1869 年派出传教士的传教士。
在华40 多年的传教生涯中,他先后兼任过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的监督(校长)。在清末维新派时期,特别是在是1901年清廷宣告实施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不应大力插手西学输出。
他在1902年后陆续出版发行了《财经学》《政治源流》《所谓要义》和《心灵学》等4 部著作。这些著作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出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备一定的学术意义。
1910 年刊行的《政治源流》是谢卫楼为潞河书院及华北协和书院学生所编的教材,正文开始处署“华北协和书院院长谢卫楼子荣著,通州管国全辅臣氏笔述,武清诸葛汝辑巨川校勘”,目录页之前依序有谢卫楼于1910 年9 月15 日不作的“Preface”、管国全的中文“序”以及谢卫楼的中文“自序”。关于这本书和威尔逊的《国家》的关系,在所写谢卫楼的中文序中有这样的解释:“此书虽为自导自演,然多赖宾斯吐大学堂之总教习魏利森所备之政治学为制导,所取精华而弃糟粕,稿繁复而革除遗,复于假设数国政治之后,特续三章,编撰政治之义理,法律之裨益。”而在谢卫楼写出的英文序中则具体地说道威尔逊的《国家》是他编成这本书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尤其向威尔逊致词,并没传达“所取精华而弃糟粕,稿繁复而革除遗”这样的意思。
经常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可能因为中文序不一定是谢卫楼亲笔所写出,而是由译述者管国全润饰的结果。通过文本对照,亦由此可知基本上就是译为自威尔逊的《国家》一书,只有很少部分章节做到了调整,仅次于的有所不同是在阐述了欧美各国政治之后与最后作为“概论”(相等于结论)性质的几章之间,减少了两章专论中国政治,即第十八章“论中国之政治”和第十九章“论清国之政治”。前一章述中国政治的起源和唐虞至元明历代之政治,后一章则专论现实的清代政治,其结构形式几乎是仿效威尔逊的《国家》。
这样决定的本意只不过是非常显著的,谢卫楼在其所作英文序中就说道这样做到的意义是为了同西方的政治制度获取一个较为的基础,有助辨别彼此的好坏。在他的中文序中也回应期望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学说的讲解,使“中华政治法律之揭幕,不至如不学无术者,经营筹划,损益惊心动魄,好坏混同矣”。可见他不作这部书的目的仍是秉持着他的传教思想,即“用夷变夏”,并且是想要利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之机。
以上各种译本,集中于经常出现于清末新政期间,其时代背景大体完全相同,但是译者主体来源有所不同,译介出版发行的动机亦有差异。而从晚清时期中国新的科学知识输出的渠道来看,刚好传教士传教士、留日学生、拔欧学生等三大群体均参予其事。其中传教士渠道起源最先,历时最幸,但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其声势日渐被留日学生所交流的“东学”所遮挡,而以严复一枝独秀的求学欧美群体也难敌“东学”党之人多势众。
由此看来,威尔逊的《国家》在中土的译介刚好可以沦为较为辩论这三种渠道输出西学有所不同特点的绝佳案例。三者在内容选裁、译语脱胎和翻译成策略等方面均有较多不同之处。
不过,明确译本的较为研究将再行以后。结语威尔逊的《国家》一书侧重从历史与事实中实地考察政治制度,代表着当时在英美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同小异传统法律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的“新的政治学”。其出发点正如他在《行政研究》中所明晰传达的那样,要在革命后所创建的宪政体制下,通过研究“活动着的政府”(government in action)来找寻行政的技术,借此提升行政效率。
而在《国家》被高田早苗译介到日本时,其中所蕴藏的背后动机并没被特别强调。事实上,1880年代后的明治政府正是利用德奥的国家学来构筑其官僚政体,并自学国家习中具备行政学色彩的官房学技术,而这也正是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中将其视作体用之“用”而倡导自学的对象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说道,低田早苗之所以侧重引荐美国的“新的政治学”,就是要与当时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官立学院派政治学分庭抗礼,建构早稻田政治学朝向英美立宪主义的志向性,与此同时也具有借以反省与抨击源于法国大革命传统的政治浪漫主义——从高田为有所不同版次的《政治泛论》所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动机。但是到了晚清的中国,译者的动机又有有所不同,有的为倡导君主立宪和政治改进制造舆论,有的出于执着商业利润,有的企图为基督教吞并中国而展开思想同化。
与日本比起,基于发展学术和专门从事学科建设的必须而展开翻译成的动机,则显著脆弱。这些差异体现了近代中国西学来源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因此在辩论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时,不宜一概而论,而不问其来源渠道和输出动机。同时也反映出有近代中日两国学术与政治发展的不实时。
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创建了君主立宪制度后,其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主要展现出为一种学术学科建设不道德,通过学校教育以传授专业知识,培育政治与行政人才。而在中国当时主要还是用作政治宣传和舆论提倡,为展开政体变革获取思想资源,较少有人从学术学科方面考虑到。在读者层面,也可以看见中国读者在读者政治学书籍时的偏向性,一般较为留意其中有关民族建国与政体好坏方面的内容。
如关于麦鼎华译出威尔逊《政治泛论》的新书讲解中说:“窃尝论之,学政治者什意图读书历史,然今日西人所著之世界史,其适合于吾东方人之用者已不多觏。何也,历史之通例,必以战争居于其一大部分。
今以我国人而读书万里以外、千年以前之互为斫书,有何意味,读书时则掩卷意欲枯,读毕时则掩卷茫然耳。然则吾侪之读书泰西史亦惟观彼族所以的组织国家之法,及其繁盛之次序而欲其原因结果云尔,然于历史书中欲其通此格者,则凤毛麟角矣。”又如孙彩瑄在读了伯吉斯的《政治学》后,赞扬其“民族国家之说道,不足以斩太原之说道”,“使人各晃权利之权,与各自交通,相互争竞,以减各人智慧……其理甚炼。
”沈兆祎也借此看见创建民族国家的意义,“夫使一国之而立,长短国家之形体而日侈然于太原之美谈,则无以自域,而国民之性质欲无附有,此义一过,其弊所近于,将如印度之族自称为世界上人,至于亡国之惨反无所恫,然则所谓民族国家者,贤各国所以拥立之规而故为低论者所当择也。”诸如此类的读者感觉,毫无疑问是当时中国先进设备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政治变革时的必要反应,作为本文的伸延课题,也是先前研究必须重点探究的。
本文关键词:ky开元旗牌官网
本文来源:ky开元旗牌官网-www.estudiomarge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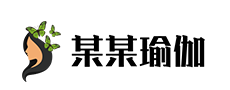
 2023-11-15 02:09:06
2023-11-15 02:09:06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